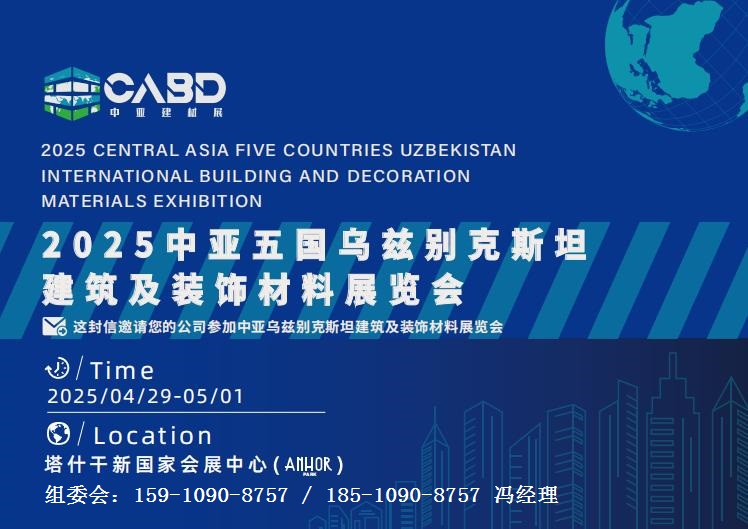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东汉时期的名臣陈蕃,言行举止可谓天下之典范。当初登上公车,手持缰绳,第一次赴任当官之时,就心怀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去豫章做太守,一到赴任之处,就问旁人:“徐稚在哪儿?”想要去拜访这位“南州高士”。掌管文书的主簿回应:“众人希望太守大人先到官署视察工作。”陈蕃说:“想当年周武王刚战胜殷商,马上就去拜访贤者商容,连休息都顾不上。我礼贤下士,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东汉时的周乘常常说:“我只要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宪,贪婪卑劣之心就会重新滋长。”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郭林宗到了汝南郡,去拜访袁阆,没有怎么停留就走了;之后去拜访黄宪,却留宿了一两天。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黄宪其人,气度内涵犹如万顷湖泊,不仅宽阔而且深邃,不受外界干扰,水清且静,无法搅浑。其器量之深广,不可估量呀!”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东汉末年的李膺风度翩翩,品行端正,对自我要求很严格。他把天下的礼仪规范、是非正义都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有许多后辈之人对其敬仰不已,能够有幸听到他教诲的,都觉得自己是登了龙门一般。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李膺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说:“荀君那种高明的见识很难被超越,钟君那种美好的德行则值得大家学习。”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太丘县长陈寔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安贫乐道生活节俭,他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陈纪驾车送他,让第四子陈谌拿着手杖跟在车后。孙子陈群年纪还小,就坐在车上。到了荀家,荀淑让荀靖迎接客人,让荀爽斟酒,其他六个儿子上菜。孙子荀彧年纪尚小,就坐在了荀淑膝上。当时太史观天象后,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有个客人问陈谌:“令尊太丘长有哪些功勋和品德,以至于他得到了全天下的尊敬?”陈谌说:“我父亲好像一棵长在泰山拐角处的桂树;上有高达万丈的山峰,下有不可测量的深渊;上受雨露恩泽,下被深渊里的泉水滋润。在这样的情况下,桂树哪里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不知道他有什么功勋德行啊!”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陈纪的儿子陈群,素有英才,一次他和陈谌的儿子陈忠各自论述自己父亲的事业和品德,两人争执不下,便去问祖父陈寔。陈寔说:“元方当哥哥很难,季方当弟弟也很难,两人难分伯仲。”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荀巨伯远行探望朋友的病,正好碰上外族强盗攻打郡城,朋友对他说:“我反正是活不成了,您赶紧走吧!”巨伯说:“我大老远过来看您,怎么能说走就走;让我背弃道义苟且偷生,这岂是我荀巨伯会干的事!”等强盗进了郡城,发现了巨伯,问他:“我们大军到了,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样的男人,竟敢一个人留下来?”巨伯说:“朋友有病,我不忍心弃之而去,宁可让我自己代朋友去死。”强盗听了纷纷议论说:“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侵入了有道义的地方!”于是就把军队撤回去了,全城也因此得以保全。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
华歆对待子弟很严肃,即使是在家里实行的礼仪也像在朝廷上那样庄严肃穆。陈纪兄弟随众人自在相处,互相关爱。但是两个家庭内部,都没有失掉安乐和睦的治家准则。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管宁和华歆一起在菜园里锄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把它像瓦砾石块一样锄掉了,华歆却捡起来又扔了出去。两人还曾经坐在同一张座席上读书,有贵人乘车摆着仪仗从门前路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放下了书出门去看。管宁就割开席子,分开座位,说:“你不是可以做我朋友的人。”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在识见和气度方面,王朗总是推崇华歆。蜡祭时,华歆曾经把子侄召集到一起宴饮,王朗也学着这么做。有人跟张华说到这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学些表面功夫,因此反而离华歆越来越远。”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华歆、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路人想搭他们的船,华歆马上表示为难,有拒绝之意。王朗却说:“好在现在船还宽敞,为什么不行呢?”后来有强盗追来了,王朗就想丢下那个搭船人。华歆说:“我当初犹豫,就是顾虑这一点呀。如今既然让他上了船,怎么可以因为情况急迫就抛弃他呢!”于是仍旧让他在船上。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和王朗的优劣。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王祥侍奉后母非常周到。他家有一棵李树,结出的李子特别好,后母一直让他看管着。有时忽然来了风雨,王祥就抱着树哭泣。王祥曾在另外一张床上睡觉,后母亲自去暗杀他;当时王祥起夜出去了,只砍到了空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为此遗憾不止,就跪倒在她面前请求她处死自己。后母因为这件事而感动悔悟,从此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晋文王司马昭说阮籍是一个最谨慎的人,每次跟他谈话,他说的话都很奥妙深远,从未评价过其他人的好坏。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王戎说:“我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从未看见他脸上有过喜悦或愠怒的表情。”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王戎和和峤同时丧母,都因为行孝而被传颂。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则痛哭失声,礼数周全。晋武帝司马炎对刘毅说:“你有没有去看过王戎、和峤几次?听说和峤悲痛的程度超过了礼数的要求,让人为他担忧。”刘毅说:“和峤的礼数虽然很周到,神智与感情却没有受损;王戎的礼数虽然不够周全,却因过于悲伤而形销骨立。臣认为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该担忧和峤,而应该担忧王戎。”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梁王和赵王都是皇帝的近亲,当时的显赫权贵。裴楷请求他们两个封国每年拨出税钱几百万来周济那些贫穷的远亲。有人指责他说:“何必跟人乞讨钱财自己做好事?”裴楷说:“从有余的地方拿些资源给不足的地方,这是天道。”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王戎说:“太保在正始年间,不属于清谈中能言善辩的人。然而一旦和他谈论起来,就会发现他的言语有理有据,意味清净深远。恐怕是他崇高的德行掩盖了他的善谈吧!”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安丰县侯王戎在服丧期间,表达孝道的情绪远远超过普通人。裴楷去吊唁后,说道:“如果一次过度的悲伤果真让身体严重损害,那么濬冲一定免不了会被世人指责为过犹不及,超出了人之常情。”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王戎的父亲王浑,素有美名,做官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有恩义的故交,都怀念他的德行和恩惠,相继一起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表心意,然而王戎谢绝了,没有接受。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刘宝曾经是一位被罚服劳役的罪犯,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把他赎了出来,之后任用他做从事中郎。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件事当成美谈。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王澄、胡毋辅之等人都把放荡不羁当作豁达,有时还会赤身裸体。乐广笑着说:“名教中自有令人快乐的地方,为什么偏要这样呢?”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郗鉴在永嘉之乱期间,住在家乡,生活很贫困,常忍饥挨饿,有一顿没一顿。乡里敬仰他的贤德,商讨众人一起轮流供他饭吃。郗鉴经常带着哥哥的儿子郗迈和外甥周翼这两个小孩去吃。乡里说:“我们各家自己都穷困挨饿,只是因为您的贤德,想合伙接济您罢了,恐怕没有办法兼顾其他人。”之后郗鉴就单独去就餐,吃完后总是两个腮帮子含满了饭,回来后吐出给两个孩子吃。大家最后都活了下来,一起过了长江。郗鉴去世的时候,周翼正担任剡县县令,他辞职回去,在郗鉴灵床前尽孝子礼,坐卧都在草席子上,深深哀悼足有三年。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顾荣在洛阳的时候,一次应邀赴宴,发现上烤肉的下人流露出想吃的神情,于是他停下吃肉的动作,把自己那一份让给了他。同座的人都笑话顾荣,顾荣说:“怎么能让人成天端着烤肉而不知肉味呢!”后来遇上战乱过江避难,经常遇到危急,总有一个人在身边保护自己。问他为什么这样,原来他就是得到烤肉的那个人。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吹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他生性极其孝顺,经常亲自给母亲做饭。平北将军王乂听到他的好名声,就送了两个婢女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男仆的身价比婢女多一倍。”祖纳说:“百里奚怎么会因为曾经被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买回去而被轻视呢!”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周镇从临川郡解任,坐船回京,还来不及上岸,船暂且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来,船很狭窄,而且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以坐下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吧!”之后立刻起用他做吴兴郡太守。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邓攸为了躲避永嘉之乱,在路上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保全了弟弟的儿子。过江后,娶了一妾,很是宠爱。过了一年,问起她的来历,她便详细诉说,自己是遭遇战乱的北方人;回忆起父母的姓名,才发现她竟然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一向德行高洁,事业有成,言谈举止都没有污点,听了这件事,终生哀伤悔恨,从此再也不娶妾了。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王导的长子王悦为人谨慎和顺,侍奉父母时神情喜悦,极尽“色养”的孝道。王导看见他就高兴,看见王恬就生气。王悦跟王导说话的时候,总是奉行谨慎细致的原则。王导要去尚书省上班,临行前,王悦没有一次不送他上车的。王悦还常常为母亲曹夫人收拾箱笼衣物。王悦死后,王导到尚书省去,上车后,一直哭到官署门口;曹夫人收拾箱笼时,把王悦收拾过的箱笼封好,再也不忍心打开。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散骑常侍桓彝听到有人议论竺法深和尚,就说:“这位先生一直都很有名望,而且前辈贤达们也经常称颂他,跟我去世的父亲也是至交好友,不应该谈论他。”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庾亮所乘坐的马中有一匹是“的卢”马,有人跟他说让他把它卖掉。庾亮说:“要卖它,就一定有买它的人,这样就会妨害他,怎么可以把对自己不利的事转嫁给他人呢!过去,孙叔敖曾打死双头蛇,以保护后来的人,这是古代的美谈。我去效仿这件事,不也很豁达吗!”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的时候,曾经有一辆很好的车,不管谁向他借车,他都会同意。曾经有个人要安葬母亲,很想借车,可是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有车,可是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就把车子烧了。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奕做剡县县令的时候,一次有一个老头儿犯了法,谢奕就惩罚他喝烈酒,老人醉得很厉害,他却还不停止惩罚。谢安当时只有七八岁,穿一条蓝布裤,在他哥哥膝上坐着,劝告哥哥说:“哥哥,老人家多可怜啊,你怎么可以太过分呢!”谢奕的脸色立刻缓和下来,说:“弟弟你想把他放走吗?”于是就把那个老人打发走了。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谢安极其敬重褚裒,曾经赞扬:“褚季野虽然口上什么也不说,可是心里像一年四季的气象那样,是非分明。”
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丹阳尹刘惔在丹阳郡任上,临终之际奄奄一息,听见供神佛的阁下正在击鼓舞蹈,举行祭祀,就神色严肃地说:“不得滥行祭祀!”属员们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刘惔回答说:“我早就像孔丘一样祷告过了,不要再做烦扰人的事了!”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安的夫人教育儿子时问太傅谢安:“怎么从来没见过您教孩子?”谢安回答说:“我总是以自身的言行来教育他们。”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晋简文帝司马昱做抚军将军的时候,自己坐床上的灰尘不许属下擦拭,见到上面留下的老鼠爬过的痕迹,觉得很不错。有个参军看见老鼠白昼出行,就拿手板打死了它,抚军很不高兴。他的门客站起来批评他说:“老鼠被打死了,您尚且不忍心;现在为了老鼠而损伤人,恐怕不行吧?”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
范宣八岁那年在后园里挖菜,误伤了手指,大哭起来。别人问他:“很痛吗?”他回答:“不是因为痛才哭,是因为身体和头发肌肤都是父母给的,不敢毁伤,所以才哭的。”范宣品行高洁、节操清廉,豫章太守韩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接受;减到五十匹,还是不接受;这样一直减半,最后终于只剩下一匹,他到底没有接受。后来韩伯有一次跟范宣同乘一车,在车上撕了两丈绢给他,说:“一个人能让妻子没有裤子穿吗?”范宣这才笑着收下了。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王献之病重,请道家主持上章消灾,按照规矩,轮到本人坦白罪过的时候,道家的人问王献之这一生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王献之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是始终愧疚和郗家离婚的事。”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殷仲堪做荆州刺史后,遇见了水灾歉收的年成,吃饭时他通常就用五个盘碗,此外就没有其他的菜肴了。饭粒如果掉在盘里或座席上,马上就捡起来吃掉。他这么做,固然是因为要给大家做个表率,也是因为他本性质朴。他经常对自家的孩子们说:“不要认为我担任了一个州的长官,就会抛弃过去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一如既往,没有改变。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怎么可以做了官就忘本呢!你们要记住我的话!”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当初,南郡公桓玄和杨广一起去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说他应该夺取殷觊主管的南蛮地区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殷觊也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于是趁着服用五石散后“行散”的机会,随便地离开了家,就不再回来了,家里家外没有人事先知道。当时他神态潇洒悠然,像古代时楚国的令尹子文一样毫无怨恨。因为这件事,当时的舆论都赞扬他。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仆射王愉任江州刺史时,被殷仲堪、桓玄率兵追逐,逃亡到了豫章,不知生死。他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听说此事后,不仅外表哀愁悲伤,同时也降低了居住和饮食的规格。当时的人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南郡公桓玄打败了殷仲堪以后,逮捕了十几个他手下的将佐,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其中。桓玄对企生一直很好,在下手屠杀之前,他派人对罗企生说:“你能向我请罪,我就宽恕你。”企生回答说:“我是殷荆州的官吏,现在荆州逃亡,生死不明,我哪有什么颜面向您请罪!”绑赴刑场以后,桓玄又派人问他有什么话说。企生回答:“过去晋文王杀了嵇康,嵇康的儿子嵇绍却做了晋室的忠臣;因此我想请桓公留下我一个弟弟来养活老母亲。”桓玄就按他的要求饶恕了他弟弟。桓玄曾经给企生的母亲胡氏送过一件羊皮袍,胡氏当时在豫章,听说了企生被害的事,当天就把袍子烧掉了。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恭从会稽回来后,王忱去看望他。看见他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子,觉得很不错,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回来,带了很多这种东西吧,可以拿一张给我吗?”王恭什么也没说。王忱走后,王恭就拿起所坐的那张竹席叫人送给王忱。这样自己就没有多余的竹席了,干脆坐在草席子上。后来王忱听说内情后,很吃惊,对王恭说:“我原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会向你要。”王恭回:“您不了解我,我做人一向身无长物。”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吴郡人陈遗,在家里最为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巴,陈遗在郡里做主簿,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布袋,每次煮饭时,都把锅巴收存起来,回家时带给母亲。后来,贼人孙恩的兵马入侵吴郡,袁山松当天就出兵征讨他们。陈遗已经积攒了好几斗锅巴,此时来不及回家,就带着锅巴随军出征。双方在沪渎开战,袁山松战败,军队溃散,大家都逃逸在山林和沼泽之间,大部分人都饿死了,只有陈遗靠着锅巴活了下来。当时人都认为这是对他纯厚孝心的回报。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
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的侍中时,因为荣幸地能得到孝武帝的恩宠礼遇而感恩戴德。孝武帝死时,孔安国任太常,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穿着重孝服,一天到晚眼泪鼻涕不断,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吴坦之、吴隐之兄弟俩住在丹阳郡官府的后面。母亲童夫人去世时,他们早晚哭吊,哀悼悲切。宾客来吊唁时,两个人跺脚号哭,哀痛欲绝,路过的人都忍不住为他们落泪。当时韩伯担任丹阳郡的长官,母亲殷氏也住在郡府中,每次听到吴家兄弟的哭声,总是为他们感到哀伤。她对韩伯说:“你将来要是有机会选拔官员的话,应该好好照顾他们俩。”韩伯自己跟他们也成了知交好友。后来韩伯果然出任了吏部尚书。这时吴坦之已经在守孝期间因悲痛而死去,吴隐之就做了大官,非常显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