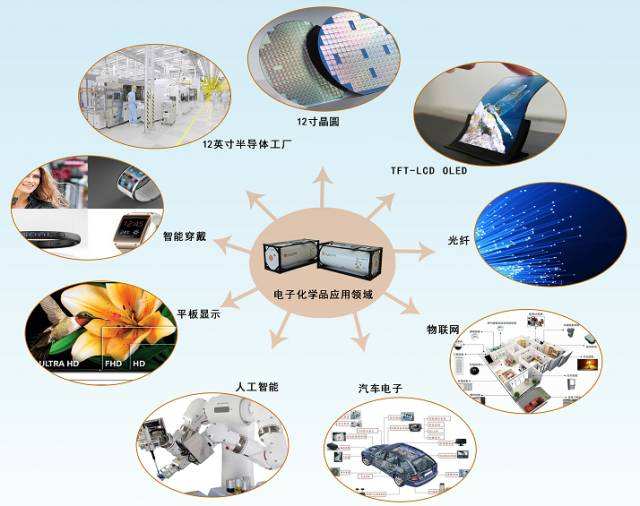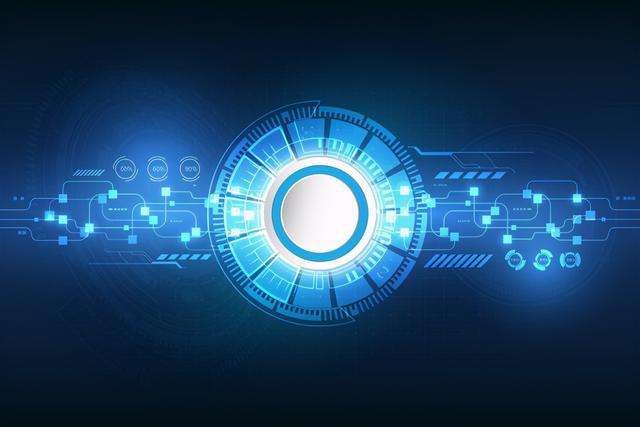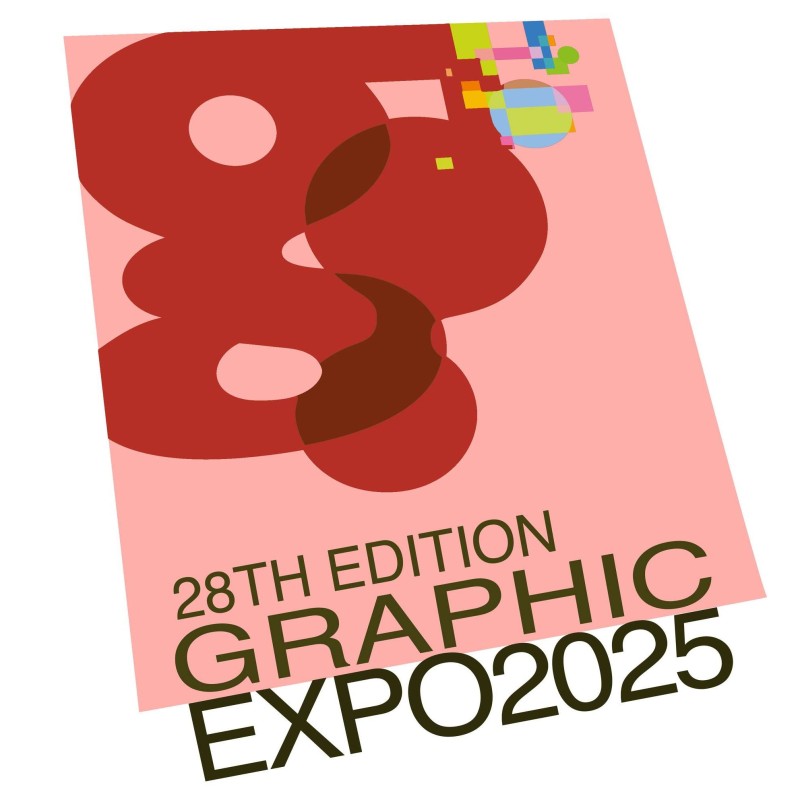在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境内,医巫闾山犹如一道雄健的脊梁,绵延挺立。医巫闾,古称“医无闾”“医无虑”等,是阴山山脉的一部分。
医巫闾山久负盛名,它曾被封为“中国五大著名镇山”(即东镇沂山、西镇吴山、中镇霍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之一。相传上古舜帝封十二神山,即以医巫闾山镇幽州之境。隋唐以降,医巫闾山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咽喉要道,是中原与东北乃至北方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关键节点。作为中国镇山文化体系的代表,医巫闾山的历史脉络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山水秩序下的医巫闾山
《国语》云,“国必依山川”。山川既是地理景观,也具有文明意义。中国传统的山川秩序,以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为中心,包含五镇、四海、四渎,形成一个超越本身自然属性、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理坐标——岳镇海渎。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都有岳镇海渎祭祀,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医巫闾山远景。 来源:北镇市文旅局
医巫闾山为中国岳镇海渎山水秩序中的“五镇”之一。《周礼·职方氏》载:“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其泽薮曰豯(xī)养,其川河泲,其浸菑时,其利鱼盐,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扰,其谷宜三种。” 《尔雅·释地》认为“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北宋郑樵的《尔雅注》解释道:“医无闾,山名,地理志云在辽东无虑县。珣,夷玉也。玗,石似玉者。琪,玉之可为琪瑱者。”由此可见,医巫闾山作为名山的历史悠久。
隋代,医巫闾山被封为四大镇山之一,因其位置偏北,遂被称为北镇。到了唐代,镇山数量由四镇变为五镇。这一时期的医巫闾山周边景观日渐增多,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之间走廊地带上的重要点位。辽朝时则将医巫闾山视为“龙兴之地”,在此修筑了十余座帝陵和王陵。
从地理角度来看,医巫闾山是从山海关进入东北后一条较大的山脉。也就是说,东北诸多山中,医巫闾山是离中原最近的一座。因其所处的关键位置,医巫闾山成为关内外交通的必经之地。有学者指出,医巫闾山可称为典型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是历史上渔猎、游牧、农耕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交汇之地。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王朝都对医巫闾山非常重视,不断加封。唐朝开元年间曾封其为“北镇爵广宁公”。辽金时期进加王号,为“广宁王”。元大德二年(1298年)封为“贞德广宁王”。明朝洪武年间称“北镇医巫闾山之神”,建庙设主,岁时祭享。清代,医巫闾山是皇帝回东北祭祖时的必经之地。据《锦州府志》记载,医巫闾山逢“朝廷有大典礼、大政务则遣官祭告,本朝亦仍旧制”。
可以说,医巫闾山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山川秩序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天下”祭祀网络的关键要素。
秦汉至辽金时期:
北镇名山的定位得以确立
在传统的九州结构中,幽州大体位于今河北以北,涵盖今北京和东北区域,是当时地理空间最东北的部分。作为幽州名山的医巫闾山,处于中国山川秩序中最偏远处,其历史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经历了变化。
秦始皇时期,将上古至周代的五岳传统与秦国最初所在的雍地诸山相结合,形成一等山川的格局,并逐步形成相应的祭祀管理制度。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颁诏,确定了五岳独尊的山川之礼,作为常规祭祀的“五岳四渎”正式成型。东晋时期,设立北郊之制,医巫闾山成为其中的从祀神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理及行政原因,中原政权祭祀医巫闾山往往只能采取遥祭的形式,对于医巫闾山的认识也更多体现在观念层面。例如,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拓跋濬巡幸辽西,其间曾遥祭医巫闾山。到了隋代,隋文帝正式下诏,定医巫闾山为北镇,正式将其列为“四镇”之一,但依然采用遥祭之法。《隋书》载:“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
辽宋夏金时期,鉴于当时多个政权并立的状态,北宋不得不沿用遥祭的办法。而位于北方的辽金王朝因为直接管辖医巫闾山区域,具备直接祭祀的条件。金朝统治者规定每逢立冬,于广宁府(今北镇市)致祭医巫闾山。这种直接祭祀活动,将医巫闾山的现实政治——地理场景与传统九州框架下的理想景观形象联结在一起。
这种观念在当时的诗文作品中也有体现,例如,金朝诗人蔡珪的《医巫闾》写道:“幽州北镇高且雄,倚天万仞蟠天东。祖龙力驱不肯去,至今鞭血余殷红……”,诗中借秦始皇传说渲染了医巫闾山的磅礴气势及其历史地位。
明代医巫闾山:
拱卫京师的重要据点
元代,医巫闾山作为边疆区域间,尤其是中原与东北之间重要节点的意义有所减弱。从总体上来看,在元朝地理时空中,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周边地区,实际上扮演了将中原地区与整个北疆联系起来的区域角色,位于锡林郭勒的元上都成为重要节点,与元大都一同构成兼容中原与北方草原的都城网络。
在明代的政治叙事中,医巫闾山逐渐成为理解当时中原与东北政治秩序的关键景观。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迁与转型。明朝建立之初,仍沿用遥祭方式祭祀医巫闾山。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医巫闾山封为“北镇医巫闾山之神”。
随着统治的逐步巩固,明朝对医巫闾山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步提升。明代官修《大明一统志》记载:“医巫闾山,在广宁卫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为幽州之镇,自是遂为北镇。其山掩拘六重,故又名六山,上有桃花洞,其中可容五六人,又有圣水盆三,其水□□岩下泄,虽冬不冰,又有仙人岩、飞瀑岩,山下有北□□□,内有吕公岩。”其中不仅记录了医巫闾山作为幽州之镇山的历史起源,而且描述了其附近的重要景点。这种在“一统志”中专门予以记录的行为,也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官方对于医巫闾山及其重要性的新认识。
明朝官员毛宪曾以“慎固藩篱”为题,指出“我国家建都,密迩北疆,设险尤宜慎重。臣尝考之,自太行西来,历居庸迩东极于医巫闾,是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是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内之藩篱,重岗叠嶂,固所调地险矣。若外之藩篱,则多有空缺之处”。其中指出医巫闾山作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与第二层之“外藩篱”,共同构成拱卫京师的重要据点。这种理念事实上是将医巫闾山作为内部圈层的地理代表,构筑了一种圈层式的地缘防卫结构,这是明朝一段时期理解中原与东北区域秩序的重要观点。
此外,明朝的一些诗作中也呈现出对于医巫闾山及其地位的普遍理解。申时行在《题清秋出塞图》中写道:“生不识医无闾,梦不到狼居胥。瞥然眎我出塞图,令我目眩心神徂……”诗中将“医巫闾”与“狼居胥”并称,把医巫闾山视为边疆景观的理念非常明显。李梦阳的《送李中丞赴镇》中这样描述:
“黄云横天海气恶,前飞鹙鸧后叫鹤。
阴风夜撼医巫闾,晓来雪片如手落。
中丞按辔东视师,躬历险隘挥熊貔。
已严号令偃鼓角,更扫日月开旌旗。
椎牛李牧将士跃,射虎李广匈奴知。
屯田金城古不谬,卖剑渤海今其时。
塞门萧萧风马鸣,长城雪残春草生。
低飞鸿雁胡沙静,远遁鲸鲵瀚海清。
不观小范擒戎日,谁信胸中十万兵。”
诗中将医巫闾山视为类似金城、塞门、长城的边地景观。许宗鲁所作的《秋晚闾山登眺》中,医巫闾山则兼具边城、名山的文化意义:
“九月边城风未寒,名山与客共盘桓。
经霜锦树真宜画,对酒黄花尚可餐。
病体不胜浮大白,壮怀犹自岸危冠。
晚来更上崔嵬石,始信人间行路难。”
跨长城内外:
清代医巫闾山的新意义
清朝最初在东北地区建立政权,于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清朝一直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有清一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先后10次赴盛京(今沈阳)祭祖谒陵。
从地理位置上看,医巫闾山正处在清朝皇帝回故地祭祖的路上,因此,清朝对医巫闾山又有新的认识。《满洲源流考》中记载:“高山肇迹,丰水贻谋,自古王业所兴,必有名山大川,扶舆蜿蟺,以翊昌运而巩丕基。我国家启宇辽东,于山则有长白、医巫闾之神瑞,于水则有混同、鸭绿之灵长,干衍支分,盘纡回缭,怀柔咸秩,笃祚万年。”
在这种情境下,高山丰水成为铸就帝业的象征。而在山水秩序当中,除了被康熙帝视作与泰山相连、具有沟通东北与中原之标志的长白山之外,医巫闾山被清朝官方认为是连接新都城北京与旧都城盛京的一个重要节点,是王朝新旧传统维系中的一处独特景观。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医巫闾山上的北镇庙,御香殿前的碑林广场立有清代皇帝的御祭、游山诗文碑。来源:北镇市文旅局
这种认识和观念在清朝历代帝王的诗作中也有呈现。康熙皇帝在《过广宁望医巫闾山》中写道:
“名山插霄汉,朵朵青芙蓉。
连亘数十里,隐现千百重。
迢遥不可及,黛色堆奇峰。
窈窕复岝㟧,郁郁多苍松。
中有桃花洞,杳霭常云封。
万古镇幽州,秩祀同岱宗。
盻望生引领,瞻顾停六龙。
何时一登览,荡涤疏心胸。”
其中既有“万古镇幽州”的历史传统的体认,又有在“秩祀同岱宗”中对其地位的进一步推崇,进而使医巫闾山成为在“瞻顾停六龙”中维系东北与中原的关键景观。雍正作有《望医巫闾山》一诗,进一步提升了医巫闾山的地位:
“翠黛满云封,遥看北镇雄。
壮观侔五岳,峻秩比三公。
葱郁兴王气,扶摇广莫风。
勒铭维祖烈,瞻仰万年同。”
清嘉庆朝本《大清一统志》中,“东穷大海,西结外藩,南邻朝鲜、渤海,北抵大兴安山,其名山则有长白山、医巫闾,其大川则有混同江、黑龙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其重险则有山海关、凤凰城、威远堡”的相关叙述,更是从“大一统”与地理时空的角度为医巫闾山作了新的定位,将其跨长城内外的普遍兼容意义凸显无疑。
自秦汉至清,历朝历代关于医巫闾山的认知变迁,事实上也是内嵌在王朝兴替史中的边疆区域间关系及其思想结构的细部呈现,反映了各个王朝尤其是“大一统”王朝对于医巫闾山所在的中原——东北空间的独特认知图景。
对医巫闾山的研究认识,从边疆思想史的维度上丰富了关于“天下”及“大一统”秩序的知识图谱。而这也正是医巫闾山能够真正超越其作为山岳本身的思想史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考古学视野下的汉晋北部边疆治理进程研究”(22YJCZH029)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海宁
制作 |章音頔
来源 |中国民族报
看完了,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