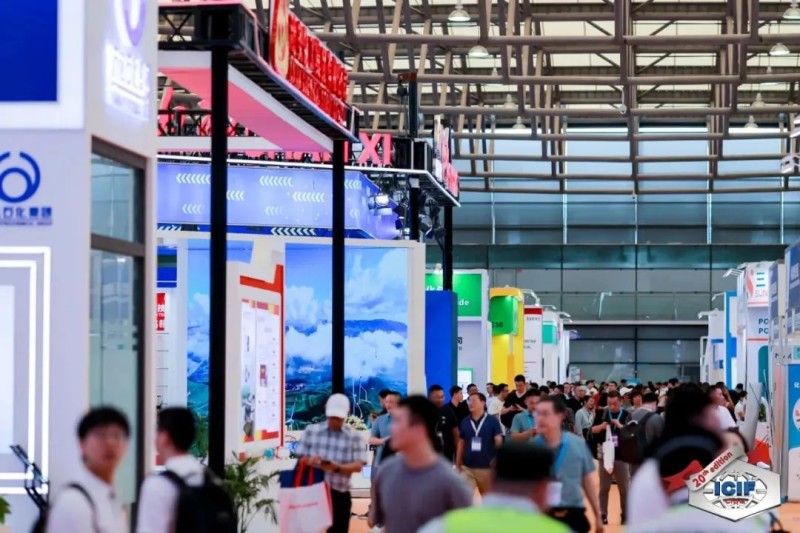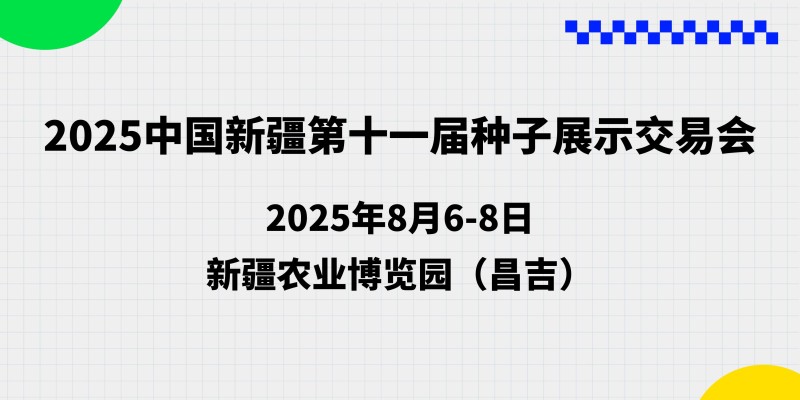还记得许多年前,一位大学同窗自外地前来与我匆匆一晤,临行时我十分郑重地送给他一份礼物:一套三册书。
以书赠人不是常规送礼路数,可在同道中人眼中,将自己喜爱且以为对方也会喜爱的书籍互赠,是江湖最高礼节,尤其是对文学青年而言。比如,更多年之前,我在恋爱时也曾赠书于她——记得是一本台湾作家许达然的散文集《如你在远方》,并在扉页题字“如你在远方,我将心向远方”。又比如,大学时一位好友自远方寄我一册钱钟书的《围城》,后来见面时瞧见他送我的那本书脏污不堪,明显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颇为不悦,给我耳提面命了一番读书人要好好爱护书籍的大道理,听得我脸红脖子粗。自那以后,他给我寄书时总是先行用报纸或日历包好书皮,令我既尴尬又感动。
扯远了,收住。现在告诉你我送给大学同窗的是啥书一一那是一套刘原的“流亡三部曲”:《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丟下宝钏走西凉》。
刘原的作品(一)
刘原,70年代生人,生于广西,现居长沙。作为一名体育记者,他曾长期追踪报道国足,以长篇报道《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名动江湖,且经常以尖锐刻薄的提问让当时的中国队主帅米卢哑口无言,下不了台,是个猛人。作为著名专栏作家,他曾在国内数十家报刊开设专栏多年,文风诡异,擅长用说段子的方式写文章,在乱哄哄的鸡飞狗跳中写出了一种根植底层的嬉皮和荒凉,让你先是扑哧一笑,继而领略文章背后深沉的意味,可谓嬉戏其表,温柔其里,触碰的不仅是你的笑穴,还有內心最柔软的地方。总之,他的文字极富想象力和黑色幽默,以乡愁为药引,以情色为味精,悲悯为底色,人送牌匾“满嘴男盗女娼,一肚仁义道德”,堪称奇文。
举几个例子吧。
在《逃向二00四年》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所谓人生,其实也无非是一场牌局。有的牌可以推倒重来,有的牌却覆水难收。正如故乡的那些街巷,门牌和街名都尽数换了,我望去只觉崭新得刺眼,我知道,真正的故乡,已经葬在记忆里了。
梅艳芳也要葬在记忆里了。10多年前,听她唱的《夕阳之歌》,只觉不如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般清亮圆润,后来慢慢咂摸,倒也品出些味道来。她和伦永亮的对唱,也是悲烈得很,像烧炙中的炭火。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夜,我在缓慢地打字,梅艳芳在缓慢地死去。从生到死,也就几百个字的距离。我敲下第一个字时,她还活着,稿子写完,她就死了。”
是不是很沉郁苍凉?
“一转眼又是阳春三月了,说起三月就不由深切缅怀雷锋叔叔。在幼年,雷锋叔叔可是我的偶像,可惜他每年都来去匆匆,所以人民群众都说他‘三月里来四月走’。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挑三月理头发,因为是免费的,那时一上街路边全是活雷锋,眼巴巴看着你,我这人心肠软,遂经常成全别人做好事的心愿。”
刘原的作品(二)
是不是很嬉皮笑脸?
……
初自接触刘原,是在《潇湘晨报.副刊》上读他的专栏文章,那样一种恣肆洒脱的文字,令我如同追星小歌迷一般,眼里金星乱窜,心里佩服得一塌糊涂,从此成为他忠实的粉丝。等到他的文字终于结集成书,也就是上述的“流亡三部曲”正式面世,马上买来一读再读还读,然后,“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象三月……”,不知不觉许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而我,也由一枚文学青年褪变成油腻大叔。
许多年过后的2023年,刘原又出了一本书一一《与尘世相爱》。毕竟年龄也大了,这一回他不再满口黄腔,而是有些一本正经,当然,那份我最喜欢的沉郁苍凉还在:
“……童年时岸边枝头的的虎头蜻蜓,少年时绿皮火车的浪迹天涯,青年时孤黄灯下的伏䅁耕作,当时都觉得是再平常不过的人生。如今回头望去,它们或许都是寻常的。但是——
已永不再来。
疫情这三年,沉痛过的人,啼哭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伤逝。
可是,我们都来过,见过繁花与落英,喧嚣与寂寥,狂欢与跌坐。那么,写下它,记住它。即便假装遗忘也背过身去抹一下眼角,它亦算是我们今生的孽缘了。
刘原的作品(三)
好好活着,去看朝露和斜阳,珍惜每一个眼前的瞬间。因为,当我们望见孩子的啼哭、潮汐的起落、花草的枯荣,那一霎,我们都处于余生最年轻的时分。
让我们继续与尘世相爱。与美好相爱。与自己相爱。”
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道是寻常却崎岖,毕竟,人生不易,活着不易。趁着还来得及,让我们追随自己的内心,去走爱走的路,去看爱看的书,去与值得深爱的人狠狠地相爱一场,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