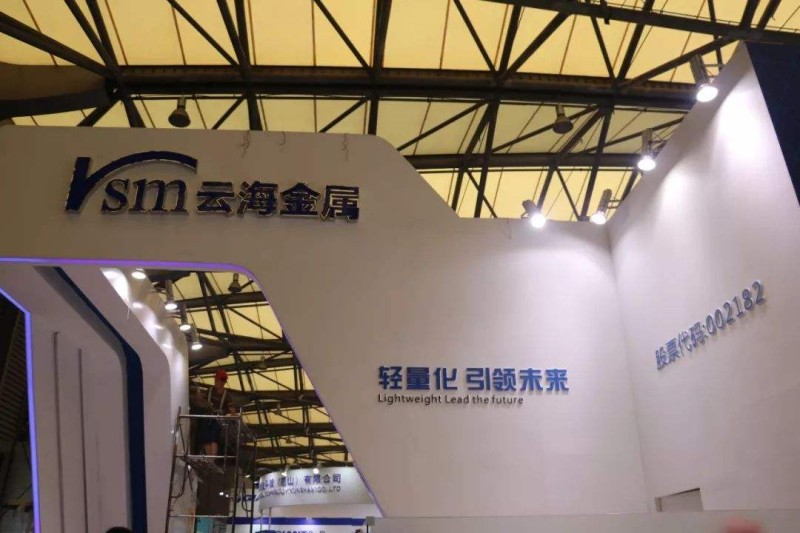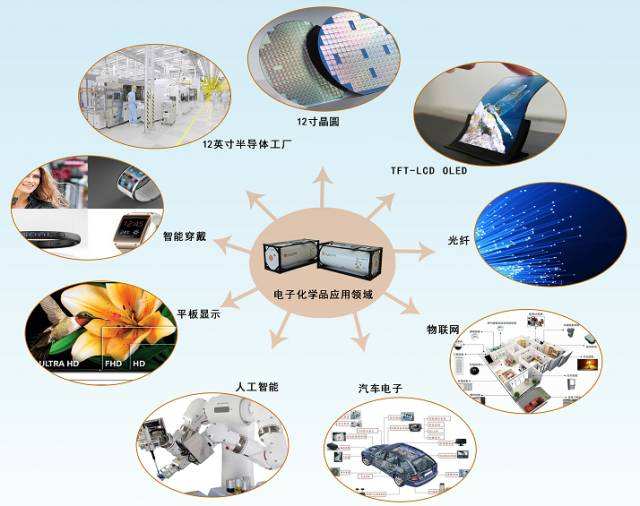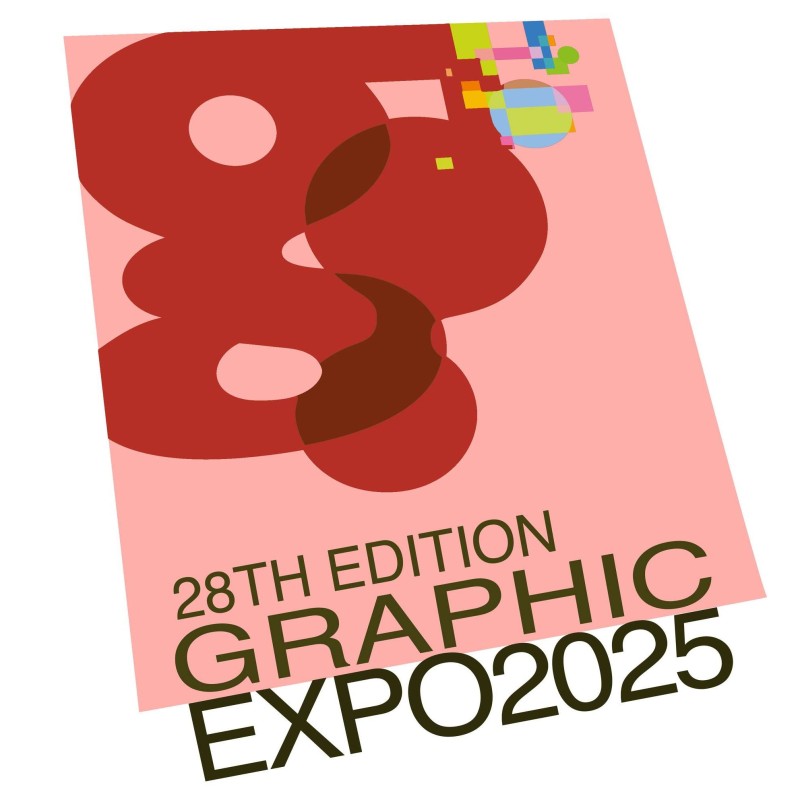重走Firenze,是要完成三个任务。
一是再次亲临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手稿,近距离感受大师的创作思路。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讲到这里想起来一件事。
本菇凉也曾是一枚艺考生,只不过备考了半个学期就转战文史科了。记得那时抓我们在画室里晚修的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她翻到素描画册里大卫像那页,啧啧道:
“好是好,就是画得太拘谨了。”
我使劲琢磨老师的话,是不是把人家皱眉的表情画得夸张了?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呢,老师接着说:
“难怪啊。别说临的了,就是这石膏像,也不知倒膜复制多少回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看看原作呢?”
想起老师的话,我特意带上70-200mm镜头到现场去,把大卫头像拍下来仔细研究——人家那是蹙眉,仿佛迎着阳光撑开双眼的状态,并没有眉头紧锁到破釜沉舟,奋力一搏的意思。
常规角度
学院美术馆里最具研学价值的,就一己之见,还是大卫像前的一组被米开朗基罗废掉的雕塑稿。
这里面就有著名的《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现原作存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内)。若是用于专业研学,一定可以看出手稿被废掉的原因。是哪里出现了裂痕?哪儿位置承重设计有风险?还是突然对姿态的设计有了新想法?手稿表面下刀痕迹全部清晰可见,对研究雕塑工艺和创作思路都是极好的教材。
作为观众,我站在这些尚未完工作品前,却有种被引领的视觉感受。
未完工的部分仿佛是大师特意留下的虚化和留白。他给足了想象空间,推动观众思考,自己去完成具像化的过程。
米开朗基罗雕塑手稿局部
学院美术馆里有个小厅专门用于展出利用放大法完成的雕塑稿。与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雕塑家大都只用泥塑或石膏完成最初的小号创意稿。真正完成作品的是学徒和工匠。
小展厅里有很多雕塑浑身上下铺满记号,像极了三维建模和动态捕捉时设定的关键点。这些当时为放大法设定的关键点,即使在今天学习虚拟建模时也有参考意义。
小样和等比例放大稿
但米开朗基罗几乎从不这样做,他是直接在石材上亲自把雕像“捧”出来的。相传,有人曾问大师挑选石材之法,想必是要讨些经验和秘笈吧。
大师说:
“他们本就在大理石里。我不过是把他们解放出来罢了。”
此言不虚。
米开朗基罗雕塑手稿局部
第二个任务,是重走乌菲兹美术馆,寻找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踪迹。
据说乌菲兹美术馆每天门票上印的作品都不一样,我们这天拿到的是利皮的作品。据说他的画作曾经几度被误认为是达芬奇的作品
利皮这幅作品最突出的创新在于溢出画框的处理方式,目的是营造一种沉浸式体验。且不说他私下里把自己的爱妻和爱子当作模特,单是这“出血”画框的构图,在当时已经是了不起的挑战了。
Madonna and Child with Two Angels
波提切利除了《维纳斯的诞生》,还有不少传世之作。发现这幅画里的人物形象相当生动
生动归生动,但终归是严肃的
作为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最后一位大师,波提切利笔下的人物总是要美的,哪怕美得千篇一律,美得端庄严肃。
左边的人物出自达芬奇之手
这幅画是经年少的达芬奇平添一笔的佳作,但要猜出哪位画中人出自达芬奇之手着实不易。如今看来,自然松弛的表情是区分的关键。
被后人笑称人间富贵花版本的拉斐尔的《蒙娜丽莎》
拉斐尔的画作里显然已看不到千人一面的美了,也许富贵花并不符合当今某些人的白幼瘦审美,但据说此画受到富商和他妻子,也就是画中人的大为赞赏。
进入巴洛克时代,画作风格更趋向情感的表达,追求瞬间定格似的力量积蓄之美。
这位女画家的成长经历坎坷,绘画成了她宣泄情绪的方式。她的传世之作在刻画人物表情方面,显然优于同时代很多男性画家。
画面内容过于抓马,就放个局部好了
能让画面极尽情绪感染力的巴洛克时期大师还有卡拉瓦乔。希腊神话里,只要被满头毒蛇的美杜莎盯上一眼,即刻就会被石化。珀尔修斯借助青铜盾牌上的映像杀死了美杜莎。卡拉瓦乔巧妙地把美杜莎被砍头时惊恐愤怒的瞬间画下来,通过盾牌使凸面呈凹面,在视觉上让美杜莎的头部向外突出,也是大胆的尝试了。
有人认为,卡拉瓦乔是照着自己的模样把美杜莎画出来的
到了卡拉瓦乔这里,绘画慢慢开始脱离传统的宗教神话题材,甚至这些题材的表现形式也渐趋于人性化和世俗化。卡拉瓦乔开始用日常生活中现实的光线表达画中的故事场景,进一步拉近画中人和画外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看标题 大概猜不出来这位画中人的身份吧?
他的画作题材里甚至出现了人们的生活日常。
卡拉瓦乔所作:算命者
回顾这两天的观展体验,我似乎顿悟了书中所提的观点。
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和回归,实际上是逐渐远离神性,人性逐步觉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