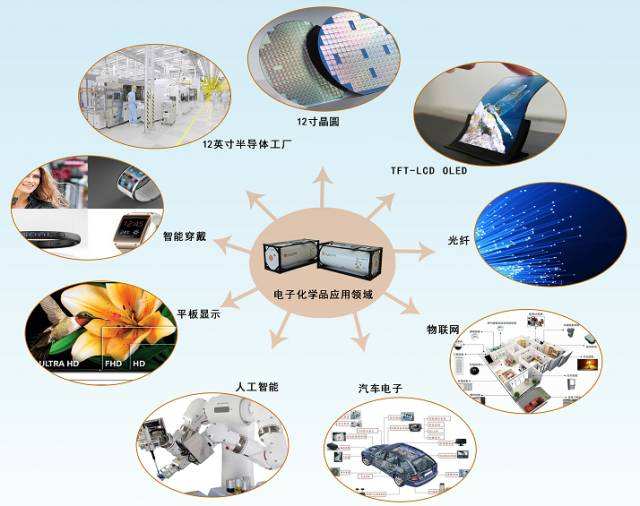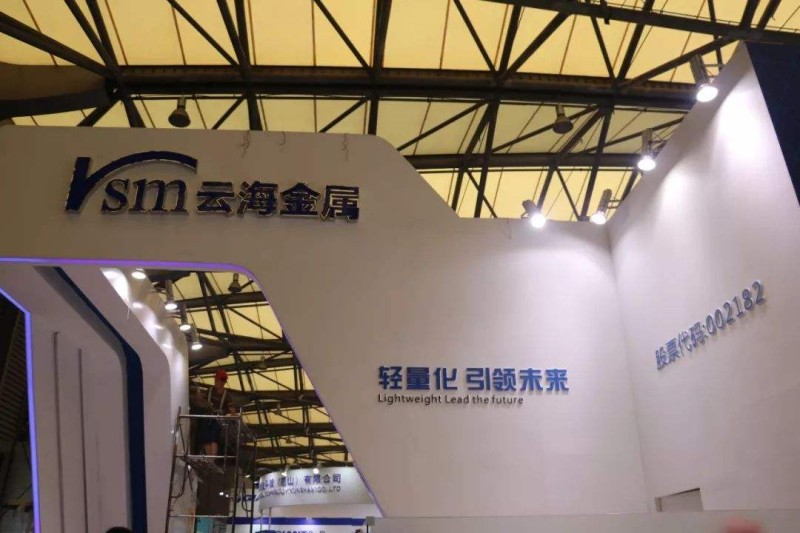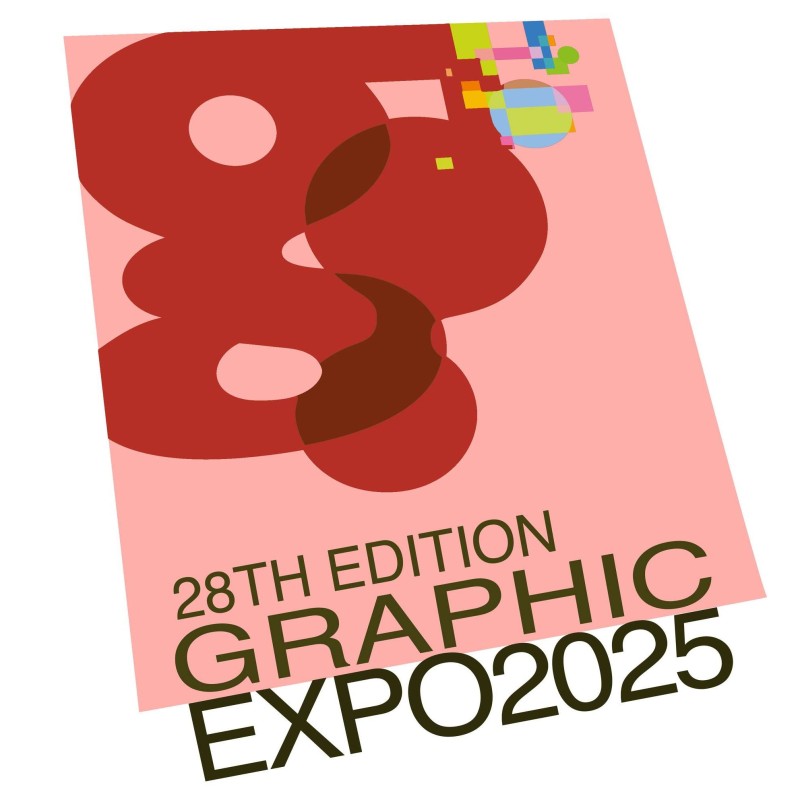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中国古典学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及其内容的学问。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多语言、多文字国家,既有大量汉文典籍,也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典籍。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典籍也属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西夏王朝除了有汉文典籍外,还有大量西夏文典籍,均应纳入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围。
西夏学在中国古典学中的地位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统治民族为党项族,境内有汉、吐蕃、回鹘等族。元朝修前代历史时,仅修宋、辽、金史,而未修西夏史,致使西夏典籍散失。西夏党项族后裔历经元、明两代,逐渐融入汉族等民族而消亡。
西夏初期,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文(当时称为番文),与汉文同时流行于西夏。西夏灭亡后,西夏文随着党项族的消亡而逐渐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清代嘉庆年间,甘肃省武威学者张澍偶然发现了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才首次识别出西夏文字。清末学者鹤龄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研究、金石学家刘青圆对西夏文钱币的研究,是西夏学初始阶段的重要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科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等人在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大量西夏文文献,在宁夏灵武也发掘出很多西夏文佛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赵元任、罗振玉等先辈涉足西夏文研究,推动了西夏学蓬勃发展。陈寅恪先生运用比较语言学、多学科综合等方法研究西夏,并培养了王静如等西夏文研究人才。王静如先生撰著的《西夏研究》三辑,标志着西夏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强调传世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出版,汇聚了中外西夏学专家的智慧,成为当时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平台。此后,因战争影响,西夏研究一度停滞。
20世纪60年代后,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王静如先生恢复了西夏研究,并招收研究生,传承西夏研究。几十年来,西夏学不断发展,获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持续取得新成就,在很多领域达到并保持学术前沿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令人瞩目的中国古典学重要学科。
西夏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出土的古代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专家们对已经消亡的西夏文字进行解读,译释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并扩展到诸多领域,包括文字、语言、历史、地理、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艺术等学科,又涉及医学、历法、建筑等诸多自然科学领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和传承,应属于中国古典学的范围。其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方法、历史考证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等,这些路径和方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展示出古典学研究的完整体系。
与欧洲古典学关系密切
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欧洲古典学经历了从新兴学科到全面研究古代文明的转变。这一时期,西夏学与欧洲古典学产生了紧密联系。欧洲学者对新发现的西夏文字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积极参与研究,与中国学者遥相呼应、相互借鉴或直接合作,共同推动了西夏学在古典学轨道上的前进。
从英国学者韦列到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再到毛利瑟、伯希和、沙畹等欧洲学者,他们对西夏文字、语言和文献的探索,为西夏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学者布谢尔对西夏文钱币的研究、德国学者本哈底夫人和查赫对西夏文字部首的考释、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言文字的深入研究等,都展现了欧美学者在西夏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
俄国学者伊凤阁在整理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时,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为解读西夏文字、翻译西夏文献提供了钥匙。他与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合作,传播重要原始西夏典籍,推动了西夏学发展。苏联学者聂斯克、龙果夫等对西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也为西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各国在西夏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西夏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吸收了欧洲古典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将其应用于对西夏文字、文献、历史的解析和研究。这种跨文化的学术互动,不仅丰富了西夏学的研究内容,而且促进了古典学研究的国际交流。
对古典学的传承与发展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夏学迎来了长足发展。学者们开始翻译西夏文文献中的原始资料,并在西夏文字、语言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更多地利用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的原始文献。新文献的发现往往能开拓古典学研究的新领域,出土的大量西夏资料是西夏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中俄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及《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原始资料,有力推动了西夏学发展,彰显出古典学以古代文献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特点。
中国学者在破译西夏文中展现出了独特智慧,深入探寻了西夏历史和社会的奥秘。近年来,西夏学家又突破了西夏文草书的识读,已有能力翻译过去难以解读的西夏文草书社会文书,为古典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资料。西夏文草书的解读不仅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深功夫,还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这也是运用了古典学研究思路和方法而取得的新成就。有些西夏文草书文献内容,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是稀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例如,西夏文军籍文书目前仅见于西夏文文献,具有特殊的古典学价值。
西夏学具有古典学文献和文物互证的特点,很多传统历史文献的记载可在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得到证实。而出土的西夏文法典的一些规定,又能在出土的社会文书中得以坐实。这种互证性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还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例如,西夏在印刷术、双语政策等方面的实践,实证了西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些西夏文社会文书,如户籍、契约等,显示出西夏存在不少族际通婚现象,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典型实例。这为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夏学利用古代文化遗存逐步复活了已经逝去的古代王朝风貌,对历史进行深度挖掘和再创造,具有古典学恢复古代社会生活、深刻认识历史的基本特点,使古典学充盈着新的生机,得以在传承中创新。
从中国古典学视角观察西夏学,可以使我们发挥古典学的优长,揭示古文字及其文献本身的奥秘,把这门既是研究对象又是工具的学问下功夫深入钻研,注重文献的深入解读,重点放在诠释古代社会生活方面,以得到有益启迪。这样能使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到重要文献的整理研究中,避免碎片化倾向。古典学视域下的西夏学是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有很大难度的学科,青年专家学者从事此类研究,要做好吃苦、下硬功夫、长期投入的思想准备。
近年来,国家特别提倡对“绝学”“冷门学科”“特殊学科”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将一批带有古典学特点的学科列入“冷门绝学”专项,给予立项资助支持。我们相信,西夏学这种具有古典学特征的学科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周学军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