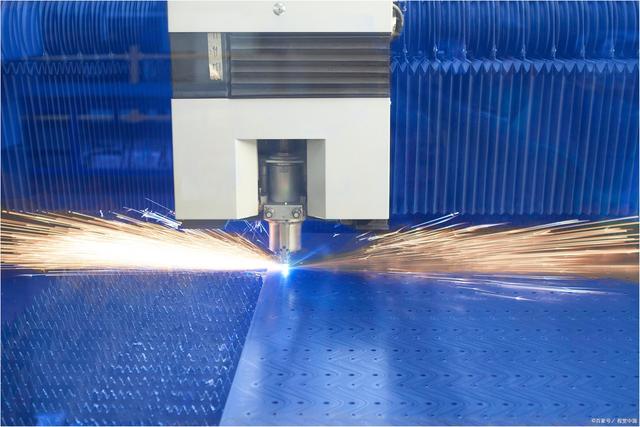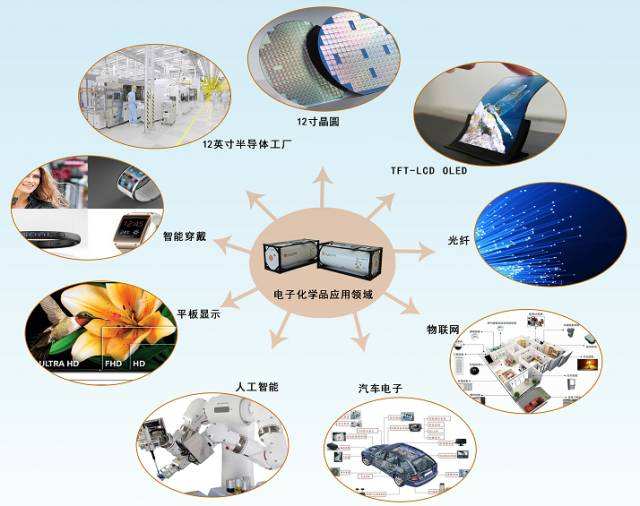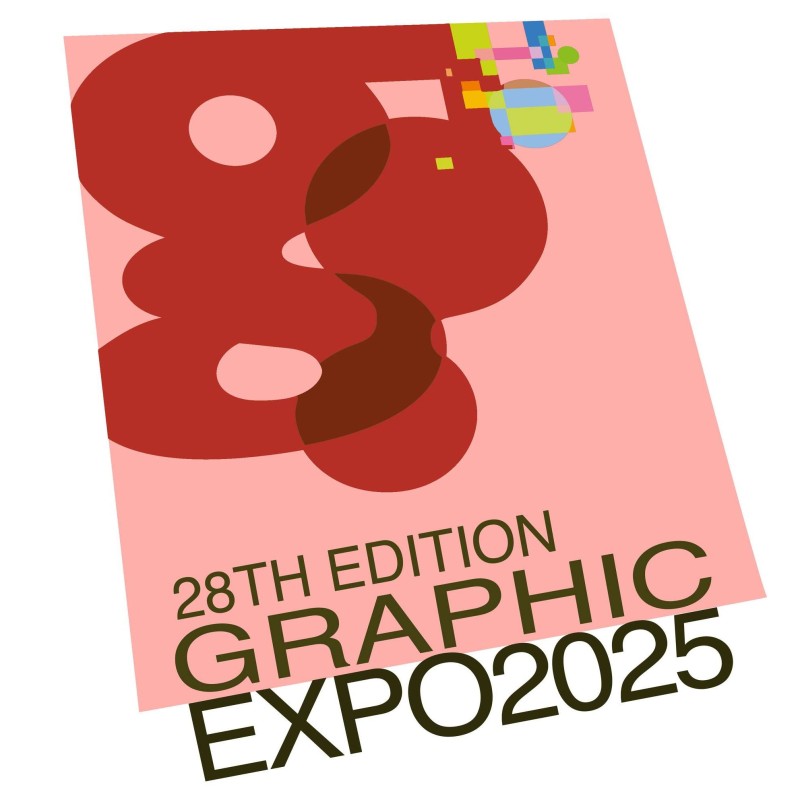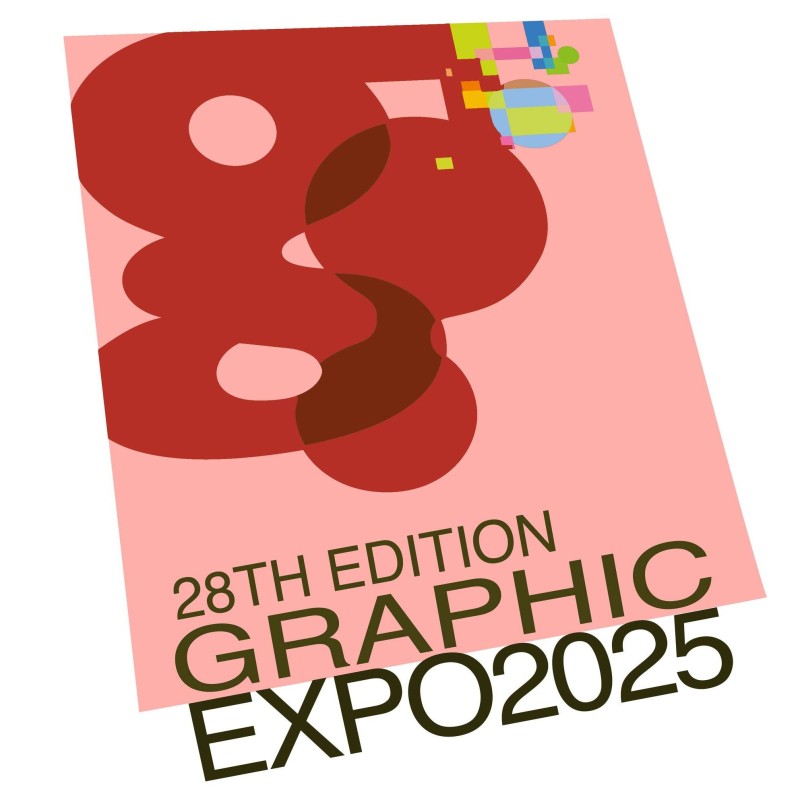1924年4月27日下午,时钟即将敲响2:00,在纽约市阿拉玛克酒店的一间大房里,俄罗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亚历山大·阿廖欣端坐在舒适的真皮座椅上,准备接受当地26位最优秀的国际象棋棋手的挑战。
挑战者坐在阿廖欣背后两张长方形桌子前,每位挑战者前面都有一个棋盘,上面摆着与阿廖欣下的棋。阿廖欣看不到任何一个棋盘。
挑战者每下一步,都由一位工作人员大声念出那步棋,使阿廖欣能够听得见,然后,一旦阿廖欣说出了自己的应招,工作人员会把这步棋摆到相应的棋盘上去。
累计有26盘棋,832个棋子,以及棋盘上1664个方格。所有这些,都不能做笔记,或借助任何其他辅助记忆工具,然而,阿廖欣却游刃有余地应对着。
这次的表演赛持续了超过12个小时,中间只吃了个简单的晚餐,等到最后一盘棋下完,已是凌晨2点,阿廖欣赢了其中的17盘棋,输了5盘,和了4盘。
这种无法看见棋盘,必须根据记忆来下棋的比赛,被称为“盲棋比赛”。
刻意练习可以将下棋水平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盲棋比赛可谓是最好的例子。
盲棋大师阿廖欣7岁时开始下棋,由于他不能把棋盘带到学校,因此,他把自己研究的棋招写在纸上,并且在学校的时候把它解出来。
阿廖欣在参加对抗赛的同时,开始对盲棋感兴趣。几年后,他自己也开始下盲棋。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下盲棋的能力,是他习惯在课堂上思考象棋招法自然而然的结果。起初,他会把招法勾画出来,然后使用自己画的草图来思考最佳招法,但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可以不用那些图来研究招法了,他可以完全凭记忆记住整个棋盘,并且在脑海中思考招法,尝试不同的对弈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廖欣能够不看棋盘,光在脑海中思考整盘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尝试着同时下好几盘盲棋。
17岁那年,他可以同时下四五盘盲棋,但他并没有在这方面追求更大进步,而是着重提高他在标准比赛中的棋艺。
1914年8月初,阿廖欣和其他许多国际象棋大师正在柏林参加一项锦标赛,恰逢德国宣布与俄国和法国交战。
很多选手都被扣留,阿廖欣因此住进了德国的监狱。在监狱里,阿廖欣发现,另外六七名最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也在那里,但他们弄不到棋盘,他们只能靠盲棋比赛打发时间。
阿廖欣上前线后,脊柱受了重伤,被俘虏了。敌人把他用铁链锁在医院的病床上,一锁就是几个月。
他又一次成天无事可做,只能靠国际象棋来打发时间,娱乐自己,他也邀请了许多当地的棋手来医院和他对弈。
在那段时间,为了让一让当地那些棋艺不高的对手,阿廖欣经常下盲棋。
后来,他同时和好几位挑战者下盲棋。他下盲棋是为了吸引人们对国际象棋比赛的关注。
阿廖欣不经意间就培养了卓越的盲棋技能。但如果你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关联实际上是一条线索,它指向一些特定的心理过程。
正是这些过程将国际象棋生手与大师区分开来,并且使大师们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来分析棋子的位置,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佳招法上。
在所有领域的杰出人物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身上具有同样这些经过高度发展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将它们作为理解卓越专家杰出能力的钥匙。
对象棋大师来讲,对手每下出一步棋,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来研究棋盘,因此,他们将准确地记住大多数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而且能够近乎完美地重新确定棋盘上最重要的区域。
这种能力,似乎否定了众所周知的短时记忆的局限。
国际象棋大师究竟是能够回忆每个棋子的位置,还是实际上只能记住当时的整个棋局,而把单个棋子的位置作为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而记住的呢?
国际象棋大师并没有培养令人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来记住棋盘上单个的棋子。他们的记忆只针对那些在正常棋局中出现的棋子位置进行记忆。
所以,有意义的记忆更高效。